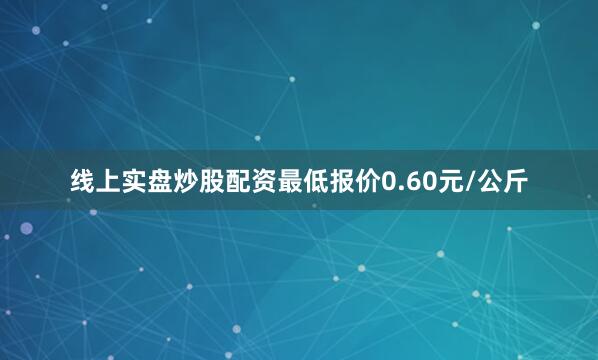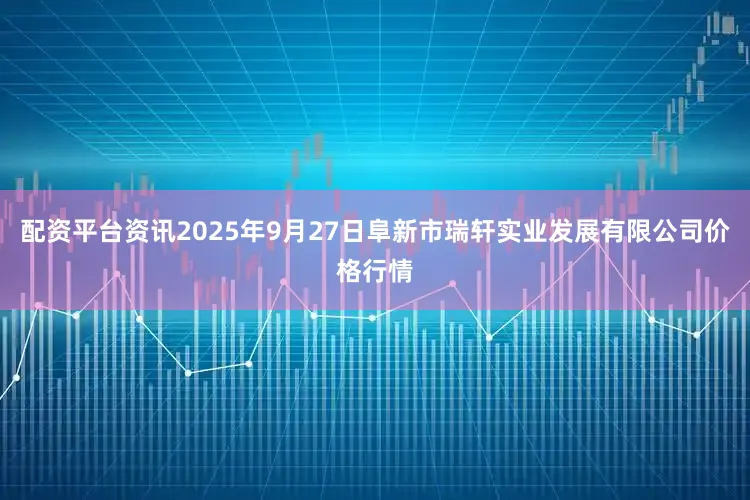1991年,苏联解体,世界格局剧变。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残躯中勉强站起,却在领土上做出取舍:放手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、亚美尼亚、阿塞拜疆,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加盟共和国,却死死抓住外东北这片从清朝手里夺来的土地。
这不只是俄罗斯的内部调整,更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,牵涉到东北亚的稳定与中俄关系的长远走向。
苏联走到解体那一步,根源在于长期积累的矛盾。1922年成立时,它继承了沙俄的大部分版图,通过加盟共和国形式把不同民族绑在一起。但到1980年代,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经济重组,试图挽救停滞的经济,却意外放开了民族分离的闸门。
展开剩余82%1990年,立陶宛第一个宣布独立,波罗的海三国紧随其后。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失败后,分离浪潮汹涌,各共和国纷纷脱离。外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独立出去的,而外东北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核心部分,从未被视为可分离的对象。
外高加索三国的脱离,暴露了苏联民族政策的局限。这些地区早在沙俄时代就被从奥斯曼和伊朗分割而来,主体民族有自己的语言、宗教和历史叙事。
格鲁吉亚以农业为主,工业基础薄弱,居民对苏联的补贴依赖有限,反而对西方模式抱有幻想。亚美尼亚保留古老的基督教传统,阿塞拜疆则深受伊斯兰影响,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格格不入。
1980年代末,纳戈尔诺-卡拉巴赫争端爆发,苏联中央调解无果,进一步激化矛盾。解体时,这些国家作为边疆加盟共和国,符合宪法退出条款,俄罗斯无力镇压,也无意强留,因为当地俄族人口虽有移民,但从未超过本土民族比例。
这提醒我们,强行整合异质文化往往难以为继,就像历史上外东北被沙俄吞并后,通过强制手段改变人口结构,才避免了类似命运。
中亚五国的独立,则更多源于经济现实。这些国家在沙俄吞并后,经历了殖民开发,但本土民族如哈萨克人、乌兹别克人始终占多数。1920年代,苏联设立加盟共和国时,就规定需位于边疆、人口过百万、主体民族过半,中亚五国正好符合。
苏联时期,它们依赖中央的资源分配和基础设施援助,哈萨克斯坦的石油、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,都融入全国分工。但解体后,俄罗斯经济崩盘,通胀率高达2500%,无力继续补贴这些内陆地区。
相反,放手还能减轻负担。中亚国家虽文化上与俄罗斯差异大,却因封闭环境,独立意愿本不强烈,但外部压力如西方援助和伊斯兰复兴,推动了分离。
相比之下,俄罗斯紧握外东北的原因,首先在于人口结构的独特性。外东北本是中国领土,历史上从扶余、室韦到女真、清朝,都在这里生息。
1689年的《尼布楚条约》确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属中国,但1858年《瑷珲条约》和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这些不平等文件,让沙俄夺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。
吞并后,沙俄推行殖民政策,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,对当地华人进行大肆清除,原住民锐减,俄族移民涌入,成为主体。
到苏联时代,这种格局进一步固化,俄族人口占比超过90%,本土少数民族如鄂温克人被边缘化。这与外高加索和中亚不同,后者原住民始终主导,分离情绪根深蒂固。
行政安排的差异,也决定了外东北的命运。苏联宪法下,加盟共和国有退出权,但外东北从未获此地位。
1920年代初,为应对协约国干涉,苏俄设立远东共和国,名义独立,实际操控,干涉结束后迅速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,成为直属莫斯科的边疆区或自治州。
1936年苏联调整结构时,中亚和外高加索升格加盟共和国,外东北却保持低级自治,没有机会成为独立实体。这种直辖模式,比沙俄时代的松散管理更高效,确保了中央的控制。这反映了俄罗斯对东方门户的警惕,避免像中亚那样因自治升级酿成分离。
战略价值的考量,更是俄罗斯不愿放手的关键。外东北拥有海参崴、纳霍德卡等良港,是太平洋舰队基地,控制着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的出入口。沙俄时代,这里就作为东方扩张的桥头堡,威慑日本和韩国。
苏联通过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和海军设施,进一步强化其作用。解体后,俄罗斯虽领土缩水,但保留外东北维持了东方影响力,否则仅靠堪察加半岛难以支撑。
相比外高加索的陆地缓冲和中亚的资源后院,外东北的海洋优势更具全球意义。这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,但也促成了中俄能源管道和贸易合作,避免了完全对抗。
这些取舍的背后,是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再到联邦的领土逻辑演变。沙俄靠武力扩张,版图达2288万平方公里,但内部不稳。苏联虽通过民族自治缓解矛盾,却在边疆制造了分离隐患。
俄罗斯的领土选择,源于实用主义:放手负担重的边疆,保留战略要地。外东北的保留,虽是历史不公的延续,却推动中俄平衡外交,避免了零和博弈。未来,东北亚稳定取决于对话,而非对抗。
现在,中俄关系虽稳固,但外东北问题如隐形荆棘,需通过经济纽带化解。这样的格局,让人思考大国间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,共谋发展。
发布于:河南省我要配资-配资炒股开户-配资平台查询网-杠杆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国内实盘交易“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”
- 下一篇:炒股配资正规平台不同领域所处阶段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