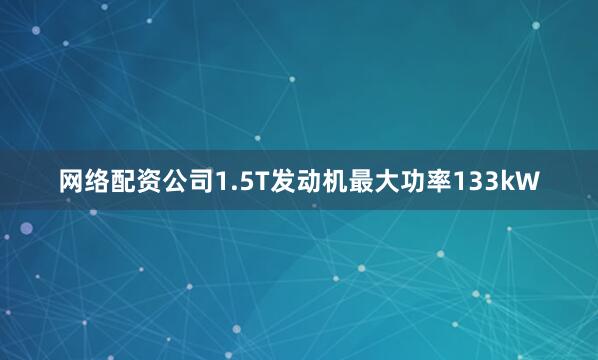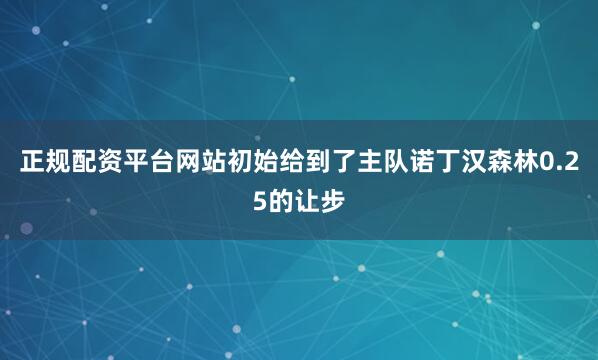西伯利亚的寒风,裹挟着1945年八月东北的硝烟味,无情地吹打着一群衣衫单薄的日本女兵。她们被苏联红军从闷罐车中赶下,蜷缩在冰冷的站台上,嘴唇冻得发紫。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试图捡起一枚掉落的纽扣,却将整片指甲粘在了冰冷的铁轨上——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,正以残酷的方式向她们宣告着何为真正的严寒。
这群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姑娘,三个月前还在关东军医院里为伤员包扎伤口,如今胸前佩戴的不再是红十字袖章,而是印着编号的劳工证。苏联人称之为“特殊移民”,档案中明确记录着:一万零三百人,目的地——伊尔库茨克煤矿。日本红十字会后来的清点显示,归国人数少了近三分之一,死亡证明上统一写着“感冒并发症”,仿佛西伯利亚的寒风能制造出千奇百怪的死法。
展开剩余75%伊尔库茨克煤矿的规则简单而粗暴:十五人一组,每日必须完成四吨的采煤任务,否则全组将面临饥饿的惩罚。护士美代子在日记中写道:“铁镐比注射器沉重十倍,掌心的血泡冻结后再破裂,感觉像戴着冰手套。”她所在的组最为不幸,连续三天未完成任务,被发配到最深、最危险的矿井。人们后来在煤渣堆中发现了她的日记本,最后几页字迹歪歪扭扭:“手指不听使唤了……隔壁组的春菜昨晚被哨兵叫走……她的棉袄还挂在我上铺……”
幸存下来的姑娘们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。日本医生称之为“冻伤恐惧症”,但这远远不足以形容她们的痛苦。1956年,东京车站的候车棚下,一位老太太听到蒸汽机车的鸣笛声,顿时将手中的热水杯摔得粉碎。她的女儿向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解释道:在矿上,这种声音意味着有人又被火车拖去乱葬岗了。更令人心碎的是社会舆论的压力,许多家属偷偷摸摸地认领她们,生怕邻居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。横滨山本家的大女儿好不容易嫁出去,婆家却发现她一见到黑面包就呕吐,第二天便退回了彩礼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东北的景象。四野卫生队收留的三千多名日本女兵,最初战战兢兢,但很快发现共产党真的会为她们提供军装。一位原关东军话务员在沈阳医院工作到退休,她的孙子多年后翻出老照片,惊叹道:“姥姥年轻时真时髦,白大褂底下穿着将校呢马裤!”这并非夸大其词,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当年积极追求日本护士,藤田嫁给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技术员,两人后来还被评为劳模。
网上流传的苏联遣返照片格外引人注目:左边是骨瘦如柴的日本女兵裹着麻布片,右边是身着棉军装的姑娘在四野医院包饺子,宛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幸存者小林昭子在晚年接受采访时,记者问她最恨谁,她一边摆弄着和服腰带,一边说道:“恨?那得有力气才行啊。我们在矿坑里,连恨都冻僵了。”她手腕上至今留有一道疤痕,那是当年为抢半块黑面包被铁锹划伤留下的。谈及在中国的生活,老太太突然笑了:“在锦州医院的时候,有个伤员教我唱《南泥湾》,现在还会哼两句呢。”
这些往事如同埋在雪地里的煤渣,看似黯淡无光,却能烧热一壶慰藉心灵的烈酒。2003年,俄罗斯解密的档案显示,伊尔库茨克劳改营的看守日志上,居然用红笔标注着“今日处决逃犯:零人”,并在下方画了一个笑脸。相比之下,日本厚生省的记录则更为残酷:回国女兵的平均寿命比常人短十二年,精神科就诊率是普通人的七倍。横须贺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娘,每年八月都会往海里撒紫菜饭团,她说这是为留在西伯利亚的姐妹们送便当。
"
发布于:四川省我要配资-配资炒股开户-配资平台查询网-杠杆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操盘推荐网这是多么可怕的人间恶魔
- 下一篇:配资论坛门户是对一个挚友的深深怀念